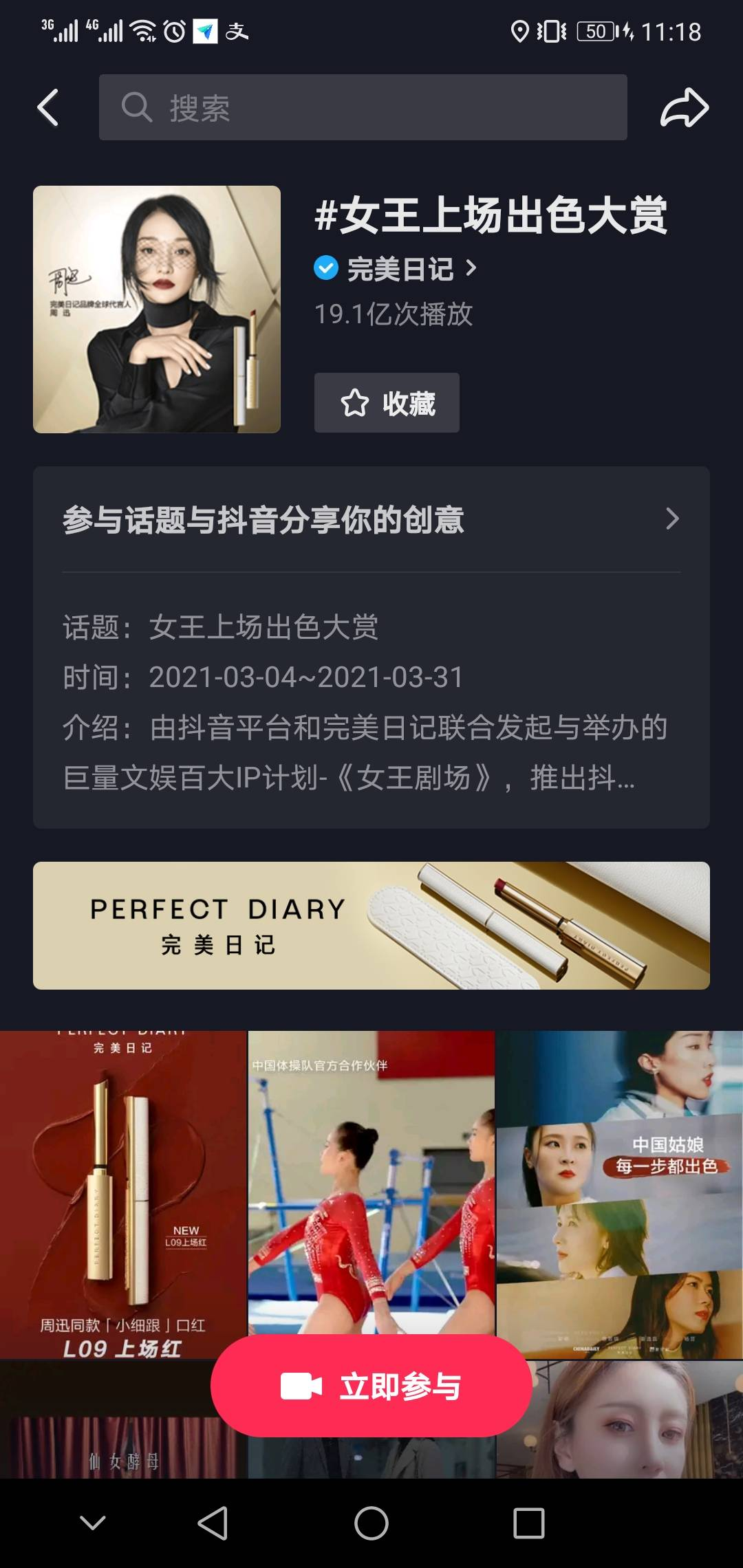小说:戴了绿帽子在线阅读「给别人戴了绿帽子会怎样」
图片来自网络侵删
我终于回了一趟耳矿,但是我回到耳矿,并不是我想念这个地方,而是师傅去世了,我回来参加他的葬礼。
打电话告诉我师傅去世的人是小铃铛,当时我正在读《涂污的鸟》。那本小说有点长,我读了三天,心里总想写点什么,所以在读的时候就有些走神。但是,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。很多次都是这样,我打开电脑,往往只写一个小说的开头,再写就兴味索然了。在我的文档里保存了好几个小说的开头,有的三千字,有的六七千字,这种半途而废让我心情郁闷。其实,我早就明白靠码字吃饭并不比在耳矿从事电焊工容易,但是我并不后悔离开耳矿。如果你在煤矿下过井,你就会理解我的心情。
小铃铛打电话给我,第一次打我没听见,当时我在厕所里。第二次打,我没接,因为那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在她第三次打给我时,我终于接了。一个人连续三次打我的手机,我想应该不是推销电话或诈骗电话。不过我可以确定这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不是我的熟人,因为在我离开耳矿后我就把手机号换了,除了我的父亲和何大伟,我没再告诉其他人我新换的手机号。电话接通后,不等我开口,小铃铛就告诉我师傅去世了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说你说什么?小铃铛说,乔师傅。我说,乔师傅?小铃铛说,就是我们在耳矿实习时的乔师傅!我说,你是?小铃铛说,我是小铃铛啊!咋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?我说,你咋知道我电话的?小铃铛说,是何大伟告诉我的。我说,小铃铛,你还好吗?小铃铛说,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,我正忙着呢。你来不来?你要是来,我们见面说。我说,我一定会参加师傅的葬礼的。小铃铛说,我读过你写的小说。我有点吃惊,因为我并没有告诉小铃铛我在写小说,而且我发表小说用的是笔名,她是怎么知道我写小说的。我含糊其辞,敷衍说,啥小说,写着玩的。小铃铛说,你应该写写我们在耳矿的事,写写师傅。我嗯了一声。小铃铛还有事,说到了耳矿见面谈,就把电话挂了。
肯定是何大伟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小铃铛。这么说我并没有责怪何大伟的意思,我拨通了何大伟的电话,他说一会我给你打过去,我正在开会。他说话的声音很小,后面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。电话挂了后,我点上一根烟,心里颇不平静,再无心思去看那本《涂污的鸟》。
我离开耳矿,师傅曾竭力挽留我。我去意已决,多说无用,师傅也就不再说什么。在我离开耳矿那天,师傅送我到火车站。我们去得早,还有半个小时才检票。我们就坐在进站口的台阶上抽烟。天有点热,我们正抽着烟,师傅突然起身,要我等一下,然后一摇一晃地离开我。原来他买水去了。他把一瓶矿泉水交给我,一只手伸进裤兜里,摸索了半天,掏出三百块钱。他什么也没说,把钞票揣进我的口袋里。我怎么能要师傅的钱呢,他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我掏出来,他按住我的手,说什么也要我带上。我只好把那三百块钱再次装进口袋里。
开始检票了,他朝我挥挥手,然后又朝我挥挥手。进了检票口,我回头去看,他正在抹眼泪。可能是看到我在看他,他对我笑了笑。我记得他当时的表情,只是想不到那一别竟成永别。
离开耳矿,我去了深圳,在那里待了半年又回来了。我回来,谁也没告诉,而是在城里租了一套小房子,开始了我自由撰稿人的生活。我没黑没白地码字,所赚的稿费勉强维持生计。有时何大伟给我打个电话,和我聊一会儿,问我什么时候回来,回来的时候好聚一聚。我没有告诉他我早就从深圳回来了,在一个距离他家不到一千米的小区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。其实,我挺恨他的,是他让我误入歧途,走上写作这条不归路的。当然,也不能全怪他,因为他也没拿刀逼着我去写什么小说。我蜗居在小城一隅,只有到了晚上才出门透口气。离开耳矿十年,除了何大伟,小铃铛是第一个和我联系的人。我们是技校同学,电焊班的,四十五个男生,只有她一个女的。按说只有一个女生的电焊班,狼多肉少,追她的人应该苍蝇一样多。可在我们班,作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小铃铛,却没有一个男生追她。不是小铃铛长得不好看,而是她太漂亮了。一个那么漂亮的女生,坐在黑压压的一群男生中,可以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,我们都知道自己配不上她,只在心里对她想入非非,但谁也没有斗胆向她表达爱意。三十多双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一块鲜美的肉,没有哪一个敢主动出击。当时的情况就是,小铃铛看不上我,也不会叫你得逞。曾经何大伟偷偷给小铃铛写过情书,被我们知道后,差点对他一顿暴打。我们把何大伟押解到技校北面的小树林里,像审问犯人一样,让他蹲在一棵树下,老实交代“犯罪”过程。
在八九级电焊班,何大伟因为写诗,故作清高,从不与我们为伍。他瞧不上我们,同样我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,你才华横溢怎么了,不也是个烧电焊的!不过客观地说,何大伟确实有点才华,虽然他写的诗我没读过,但是他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诗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不是发了一首,而是一组诗歌。何大伟十七岁就在《诗刊》发表作品,可以说是少年得志,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行事低调,诗歌发表后他并没有四处宣扬。要不是同样喜欢写诗的魏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,我们会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魏老师教我们政治,写诗多年,只在一些小报刊发表过诗歌。当他看到何大伟发表在《诗刊》上的那组诗歌后,他兴奋地来到我们电焊班,一进门就大叫,谁是何大伟?
刚才还吵吵嚷嚷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,我们看着魏老师,看着他举在手上的那本杂志。何大伟站起来,说了一声我是何大伟。魏老师朝何大伟快步走过去,等他走到何大伟的座位前时,魏老师握住了何大伟的双手,说何大伟同学,你发表的诗歌我读了,写得太好了。魏老师兴奋而又激动,松开何大伟手,翻到刊载何大伟诗歌的那一页,说下课后到我办公室一趟我们聊聊。
何大伟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诗歌,不亚于在我们中间突然放了一个雷子,炸得我们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这个雷子的杀伤力太厉害了,不止如此,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小铃铛居然主动跟何大伟示好,向他要了一本诗刊。这让我们四十三个男人妒火中烧。如此下去可不行,我们觉得应该找个借口把他好好教训一顿,让他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理由总会找到的,他写情书给小铃铛,这个举动足够我们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。
如果说何大伟是才子,那小铃铛就是佳人。文学作品都是这么写的,才子配佳人,但是我们却不那么想,我们得不到的,就算你何大伟才高八斗,也别想抱得美人归。我们要他交代情书里都写了什么,可他紧要牙关,就是不说。他视死如归,让我们恼羞成怒,就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。是李志强提出脱何大伟的裤子的,他那么说,我们纷纷响应,七手八脚把何大伟按在了地上,有按脚的、有按头和胳膊的。何大伟蜷缩起身子,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声。那一刻何大伟斯文扫地,再也不是那个狗眼看人低的才子了。
在李志强扯下何大伟的裤子时,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这个家伙居然小便失禁了,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的鸡鸡小得出奇,比三岁小孩的大不了多少。我们愣了一下,谁都没有说话,似乎是集体失声了。何大伟躺在地上,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不知所踪,那一刻他狼狈不堪,比一只丧家犬好不到哪里。我们突然就兴味索然了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然后勾肩搭背地离开了那片小树林。我回头看了一眼。何大伟还躺在地上,两只手捂在腿间。斑驳的阳光落在他的身上,轻轻地晃来晃去。
第二天,何大伟没有去学校,第三天,他也没去。等他再次出现在电焊班的教室时,已是七天之后。我们看着他走进教室,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,然后看着他挨个座位发烟。一包烟发完,他又掏出一包。但是,我们没抽他发的烟,而是夹在了耳朵上,看着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。只有小铃铛不明就里,她看看我们,又看看何大伟,说何大伟,你怎么回事?何大伟不理她。小铃铛说,何大伟,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?何大伟还是不理她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物理老师走进了教室。物理老师看到我们耳朵上夹的香烟后,她先是愣了一下,接着大吼了一声:谁让你们把烟带教室的?我们只好把夹在耳朵上的烟收了起来。
这个何大伟太让我们失望了,其实我们是多么希望他和过去一样,目空一切地走进教室,而不是与我们同流合污、沆瀣一气。何大伟不该与我们和解,作为一个诗人,他应该有点气节、有点傲骨,不该向我们妥协。下课后,我们去了操场,坐在树下点上了何大伟给我们的香烟。我们正抽着烟,何大伟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他在我的身边坐下,也点上了一根烟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,什么也没说。从那以后曾经特立独行的何大伟,不再写诗,也不再想入非非。他私下里写不写诗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技校毕业,我和何大伟,还有小铃铛分配到耳矿去实习。耳矿是一个小矿,地处偏远,年产量三十万吨,因为是薄煤层矿井,条件艰苦,效益比不得那些大矿,而且交通也不方便。从县城坐公交到镇子上,还要再走五六里才能到。我们当然不会走着去耳矿,到了镇子上,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。去耳矿的路坑坑洼洼,拉煤的大货车开过去,黑色的煤粉便会落一身。家里有关系的同学,都去了大矿。那些年产几百万吨的大矿,不仅环境好,效益也好。我们三个人被安排到耳矿去实习,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何大伟、小铃铛同我一样没有社会背景。说不定在实习结束后,我们会就此待在耳矿。何大伟似乎并不在意,他比小铃铛乐观多了。坐在三轮车上,我和何大伟抽着烟,但是我的心情不怎么好,因为我父亲就在耳矿工作过,矿上的条件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耳矿男多女少,想在矿上找对象,根本不可能,所以很多矿工找的对象都是农村的。
去耳矿的路上,小铃铛撅着嘴巴,啥话也不说。我问她怎么不说话,她把眼一瞪,没理睬我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小铃铛,我感觉她没过去那么漂亮。因为离得近,我甚至看到了她脸上的雀斑。我数了一下,至少有十几个雀斑,而且她的嘴唇还有点厚。在学校时,她可是我电焊班倾国倾城的美女。怎么仔细一看也不过如此呢。发觉我在看她,她对我翻了一个白眼,说看什么看!又不是不认识!我讪讪地一笑,说小铃铛,你这是干嘛啊!我们只是来实习,又不会老死在这里,用得着哭丧着一张脸?小铃铛说,叫我名字!以后你再叫我小铃铛,小心我割掉你的舌头。
我说,好!金铃子同学,以后我不再叫你小铃铛了。
小铃铛皱着眉头,一直到了矿上都没再吱声。
小铃铛的名字叫金铃子,因为她说话声音脆生生的,犹如银铃声,我们给她起了一个小铃铛的绰号。这个绰号在电焊班传开后她并生气,同学三年,我几乎把她的名字给忘了。其实,金铃子这个名字也很好,只是我一时改不过口来,在耳矿实习期间,还时不时地叫她小铃铛。
我们去矿机厂实习,矿上安排老乔做我们的师傅,而且还签订了师徒合同。乔师傅在井下干了不到十年,因为工伤从井下调到了矿机厂。刚到矿机厂他只是干杂活,后来自学电焊,考了电焊证。我们认他做师傅时,他已是八级电焊工,在矿机厂焊工一流。那是一个其貌不扬,还瘸着一条腿的男人。在矿机厂,谁都可以和他开玩笑,而他一点也不恼火。但是,他对我们却不苟言笑,总是板着一张脸。我和何大伟背地里叫他乔瘸子,小铃铛却从不叫他瘸子,而是毕恭毕敬,一口一个师傅。乔瘸子呢,可能是因为养了两个儿子的缘故,拿小铃铛当闺女一样对待。对我和何大伟,乔瘸子只会安排我们干脏活累活。我们心里有怨气,但又不好说出来。小铃铛是一个女孩子,当然需要照顾一下,我们也就不去计较。况且她也好不到哪里去,穿着矿上发的工作服,松松垮垮的,再看她哪是当初我们梦中的女神。
在耳矿实习期间,何大伟每次回家都带回一摞书,但不是文学书籍,而是一些自学考试的书。白天干一天活,下班回来他也不休息,拿个纸箱当桌子,趴在上面看书。我闲得无聊,在宿舍呆着又没意思,就去别的宿舍打牌、喝酒。半夜回来,我看到何大伟还在读书,不再理他,倒头就睡。何大伟看书很用功,就差头悬梁、锥刺股了。
第二天,我一直睡到上午十点。我醒来的时候,何大伟不在宿舍。我翻个身,又想睡,于是我看到了那本厚厚的《罪与罚》。我不想起床,就翻开那本书看起来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外国人写的书。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,午饭也没吃。到了晚上,我才去食堂打饭,吃完又看起来。晚上八点多,何大伟回来,听到开门、关门声,我把书搁下,对他说,这书挺好看的。
何大伟说,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呢。
我说,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太长,不好记。
何大伟说,看多了就记住了。
我又去看那本《罪与罚》,用了三天时间终于看完了。看完后,我问他还有别的书吗?何大伟又给我一本《远大前程》。后来他回家又带来一些杂志,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。看书让我感觉充实了很多,正如何大伟说的,趁着年轻,多看点书没坏处。何大伟不再写诗,他要参加自学考试。他看过很多文学名著,也买了不少,他看过的那些书,后来都送给了我。他还鼓励我写小说,但是我一直不自信,上学时我最怕写作文。我写小说,那还不是赶鸭子上架,自讨苦吃。过去在电焊班,我和他接触不多,想不到住一个宿舍后,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。我很想就那次在小树林发生的事向他道歉,但是每一次都欲言又止。那是他的伤疤,旧事重提,不亚于再揭伤疤,所以很长时间里我心怀愧疚。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动手,而是站在一边看着。作为一个看客,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,再说我们那时少不更事。这么一想我又释然了,说不定何大伟已经在心里原谅我们了。
因为晚上看书,睡得晚,白天便没有精神,到了班上就打瞌睡,师傅安排我干活我就心里烦。那个时候师傅也烦,矿上农转非,但是需要在井下干够十年才符合条件。师傅只在井下干了九年,还差一年,他想再去下井,但是矿上不同意。师傅心烦,看我就不顺眼。何大伟背地里对我说,别顶撞师傅,他有难处,心里窝火。我说,管我什么事啊!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。何大伟说,师傅两个儿子,一个脑瘫,一个学习不好,他天天犯愁呢。这个情况我不知道,问何大伟是怎么知道的。他说是小铃铛告诉他的。
我说,耳矿有什么好的,就算农转非来到矿上又能怎么样?
何大伟说,总比在家种地强吧。
师傅四十多岁,活了一把年纪了,人情世故应该懂得一些,但他那个人一根筋,连送礼都不知道。还是在别人的指点下,师傅一咬牙,买了两瓶茅台。在送礼之前,师傅很是犹豫,问我和何大伟,这礼怎么送?我和何大伟都没给人送过礼,也不知道怎么送。师傅叹口气,说办点事怎么这么难呢。
何大伟说,师傅,徐矿长那个人除了喝酒没别的爱好,所以送酒给他,是投其所好。其实,以前他不喝酒的。他之所以喝酒是因为他的老婆。徐矿长的老婆在县医院工作,两个人是高中同学。但是,结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怎么好。徐矿长一个月回不了几趟家,他们要是关系好,徐矿长会经常回家的。
我说,大伟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?
何大伟说,师傅,情况就是这样的。你送酒给他,他肯定会接受的。
我说,师傅,你要是不好意思,我同何大伟跟你一起去。
何大伟说,又不是去打架,去那么多人干什么,送礼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们要是一起去,人家不会收的,说不定连门都不会开。
师傅说,我也这么想的,只是我担心人家把我拒之门外。
何大伟说,师傅,你别提送礼的事,只说串门。
师傅点点头。
天色渐暗,我们跟着师傅,拎着那两瓶茅台,去给徐矿长送礼。一路上师傅都在说自己紧张,送个礼咋感觉像做贼一样。我们就笑他,说师傅,你只是去串个门。伸手不打笑脸人,何况你是去送礼。
师傅说,可我就是紧张。
到了矿招待所的楼下,师傅紧张得两腿发软,要打退堂鼓。来都来了,不能再回去吧。我掏出烟来,递给师傅一根。师傅点上烟,狠狠抽了一口,说是死是活由他去好了。何大伟说,师傅!这又不是生死攸关的事,你放心!多大的事啊。
师傅说,我这辈子没求过人。
我抬头看了看二楼,206房间亮着灯,说明徐矿长在房间里。师傅也抬头看了看。小铃铛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们一跳,她不明就里,问我们站在楼下干什么?师傅支支吾吾,没说送礼的事。小铃铛也住矿招待所。她一个女生,矿上考虑到她住单身宿舍不安全,就把她安排到了招待所。小铃铛看看我,又看看何大伟,说你们有事?
何大伟说,你小声点。
小铃铛说,你们三个人鬼鬼祟祟,是不是想干什么坏事?
我说,你怎么和师傅说话?
小铃铛说,我没说师傅。
何大伟说,徐矿长是不是住206?
小铃铛点点头,说刚才我看见他了。
我说,师傅,你快去吧。
师傅说,那我去了。
去吧!我们说。
师傅拎着两瓶茅台酒,一步一回头,像要去刑场。看着他上了楼,在楼梯的拐角,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,然后消失不见了。
小铃铛又问我和何大伟师傅去干什么?我们只好实话实说。小铃铛听后笑起来。我们问她笑什么?她说,我还当你们要干什么坏事呢。我说,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,能有什么坏事可干啊!小铃铛说,那可不一定。我们正说着话,师傅回来了,空着两只手。徐矿长把两瓶茅台酒收下了,看来有戏。师傅一头汗,见了我们,说我们回去吧。
何大伟说,徐矿长怎么说的?
师傅说,他说他会尽力的。
我说,只要他收下礼物,这事肯定没问题。
师傅说,但愿如此吧。
我们没有回宿舍,因为师傅说还没吃晚饭,他请客,在矿门口的饭店吃一顿。我们跟着师傅去了矿大门口。小铃铛没去,她回招待所睡觉去了。
喝下半斤酒,师傅告诉我们,他之所想办农转非,主要是因为老婆孩子在家总是受欺负。老婆带着两个儿子,大儿子脑瘫,小儿子才八九岁,而他一年里回不了几趟家。要是农转非来到矿上,他老婆可以找个临时工干,而且以后还能分到房子。同老婆孩子在一起生活,那才是一个家。
那个晚上,师傅喝多了。我和何大伟喝得也不少,因为喝了酒,师傅的话多了起来。当时我喝得晕晕乎乎,没在意师傅所说的。到了第二天,睡醒后,我躺在床上把师傅晚上说的话又回忆了一遍。但是,我只记得师傅说他的那个小儿子,长得一点不像他。我看了一眼躺在对面床上的何大伟,他正在看书。
我说,大伟,师傅昨晚说他的小儿子不是他的,是我听错了吧。
何大伟说,你没听错。
我说,师傅被人戴了绿帽子。
何大伟说,所以你结婚后最好不要两地分居。
我说,结婚?我和谁结婚?
何大伟说,早晚你都要结婚的。说完这话,他又低头去看书。
何大伟不再写诗,却怂恿我写小说,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我是写小说的料吗?我有些怀疑自己。可他却说,你不写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料。他说的不无道理,但我还是信心不足。我问他怎么不写诗了?他说等他自考完了再说。何大伟不写诗,不等于他不写别的。在耳矿实习期间,他写的新闻报道在《中国煤炭报》发表了两篇。看他是个人才,矿宣传科的科长找到他,同他商量,以后就在耳矿干,以后会把他调到宣传科从事宣传工作。这种好事,可是天上掉馅饼。何大伟没有理由不同意。
我们实习结束,回到学校,等待分配。正如我想的那样,何大伟、小铃铛,还有我,被分到了耳矿。我们学的是电气焊,矿机厂只有师傅一个人从事电焊工作,活多的时候,他天天加班,所以理所当然我们又回到了矿机厂。上次是来实习,这次来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们要在这里工作,与耳矿同生共荣,一直干到退休。这么一想,我就害怕。但是,小铃铛不一样,她是一个女的,即使师傅不偏爱她,也不会让她干脏活、累活,平时只给师傅倒个茶就行。我和何大伟不一样,我们是重点培养对象,而何大伟和我又不一样。矿宣传科已答应他,只要他好好写新闻报道,调到宣传科是迟早的事。只有我前景黯淡,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和师傅一样干到老。这样一想,我就悲观绝望。
我们再次回到矿机厂,最高兴的人是师傅。让师傅高兴的是不仅是我们回来了,还有他的农专非的事。矿上在秋天张榜,名单中有他。下一批农转非,师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,就会来到矿上。徐矿长那个人还是说话算话的……
——未完待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