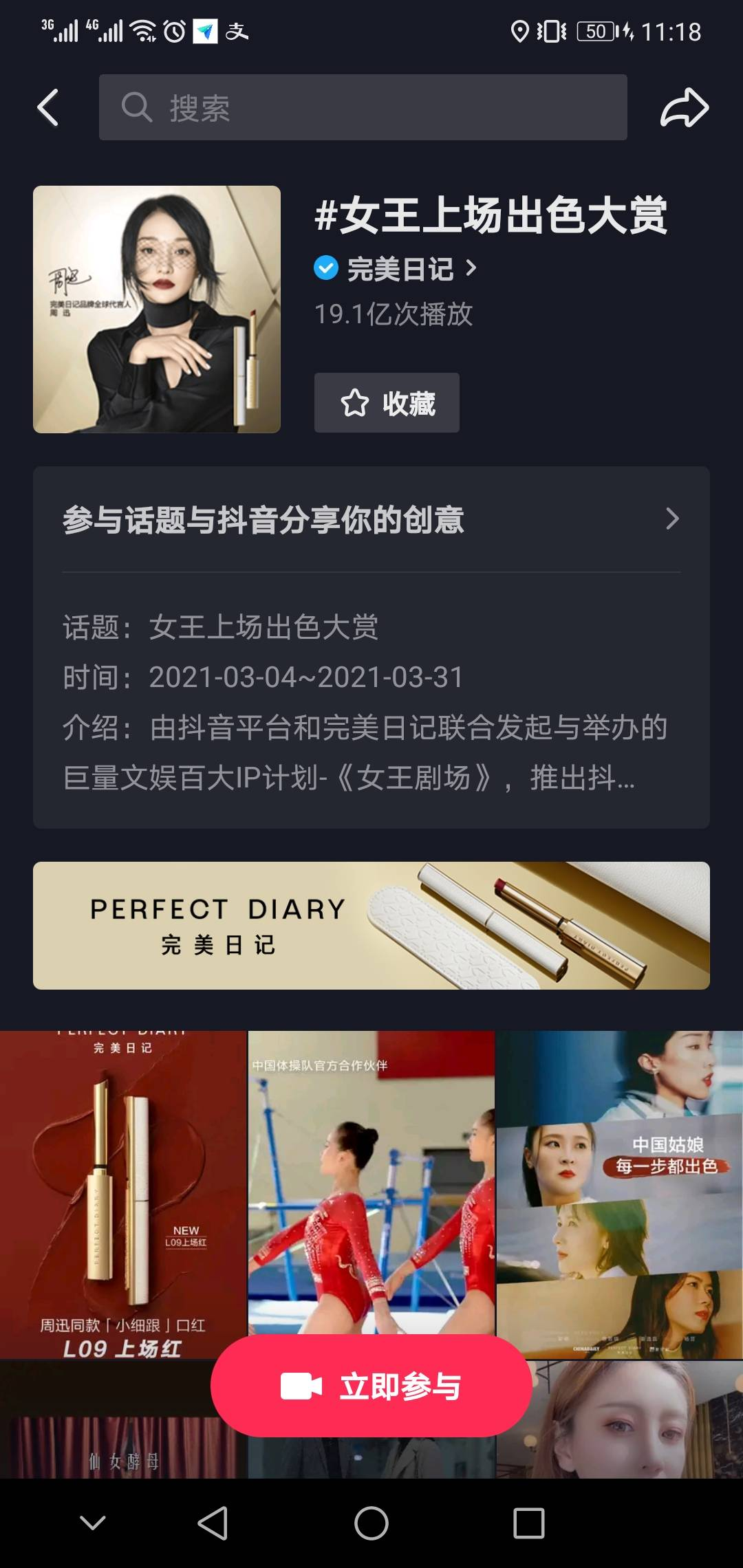子不嫌母丑夫不嫌妻丑「又黑又丑又臭」
世人皆知,盗帅楚家后人,踏月留香,素手取物,从未失手过。
我没料到,自己会成为终结这句话的罪魁祸首。
其实出发前长老早已再三叮嘱:“楚欢欢!这次再闹幺蛾子耽误了时辰,你藏在厨房灶头下的私房钱就全部充公知道吗?老祖宗的规矩,说好子时,那就少一分多一毫都不行!”
私房钱是我的命根子,谁敢充公我跟谁急,但长老淫威在上,我只是讪讪解释道:“长老,这人有三急我也无可奈何嘛,我就不信风流倜傥的老祖宗没有吃坏肚子的时候!”
长老震怒:“你还有理了——你看看你,膘肥体壮的,咱们楚家纤细风流的劲都给你败坏得一干二净,你还居然有理了!”
我气极,将我的珠圆玉润污蔑成膘肥体壮,你就有理了吗?
长老怕我误事,提早将我赶出家门早早地守在蹲点的地方,只等时辰一到,便翩翩出场,踏月而来,请走那副白玉雕成的青玉棋盘,但四月,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,特别是晚上,凉风猎猎,我蹲在树上没一会儿,便直感肚内一阵绞痛——
我大惊,这可不是月事要提前汹涌而来的前兆吗?
月事有三宝,红枣姜茶益母草。
没有这救命三宝,我压根连床都起不来,我自觉倒霉,但没料到,倒霉一般都很成双成对,绝不形单影只。
这次王家请来坐镇的,居然是六扇门的人。
夜幕四合,东阳王家的大院却灯火通明,亮如白昼,数百有备而来的家丁举火把围在藏宝阁院中。我将棋盘拿到手,尽管此刻下腹绞得痛不欲生,面上依然装得格外孤傲,此时院内几人,面孔硬朗,都穿过膝长的黑衣,腰带上挂着六扇门字眼的牌子。
出门不利,何等堪忧!我猛地收住怯意,一身轻白锦绣长裙在寒风里猎猎飞舞,将我楚门遗世独立的范儿展现得一览无余,我冷冷做俯视众生的样儿,淡道:“诸位何必舞刀弄枪,坏了今夜如此月色,在下楚门……”
话音未落,一帮如狼似虎的六扇门高手十指微屈,如猎鹰般猛攻而来,列七星灭天阵,招招致命,剑影如电,由四面铺天盖地刺下,眼更似鹰目,仿佛要将我凌迟百遍。
不对劲,有哪儿不对劲啊。我节节败退时,大感惊恐。
东阳王家不过是当地书香世家,朝中无势,怎能请得动远在京师的六扇门。
这副视她如杀父仇人欲杀之而后快的气势究竟是怎么回事——
就在我体力不支,腹痛得几欲晕厥的一瞬间,其中一铁汉单手扼住我咽喉,倏地将我整个提起,面容冷酷至极。
“告诉兄弟们,玩弄咱们门主的小贼,已经找到了!”
误会,我这种膘肥体壮的身形,能玩弄谁啊!
我简直委屈得肝肠寸断,这的确是天大的冤案,我连六扇门门主的样貌都没见过,谈何玩弄!
这时,监牢外的那条深不见底的长廊外哐当一声,牢门从外打开,紧接着是一阵咕噜辗地的声音,一名六扇门捕头毕恭毕敬地推着一把轮椅缓缓进来,轮椅上坐着的青年乌发垂肩,双膝上盖着条薄羊绒毯,青年略一挥手,那捕头便恭谨退下。
那青年双手闲适搭在轮椅两侧,露出骨节分明却苍白的手,墙边两侧的烛火忽明忽暗地勾勒出那青年的容貌,竟是少见的肤白俊目,长眉入鬓,眉宇泛着冷肃,像一把寒光凛冽的剑。
青年嘴角一动,虽言语带笑,但衬着这阴暗莫测的牢狱,越发让人毛骨悚然:“楚小姐,三年不见,如今可好?”
我退后数步,狐疑道:“哥们,你谁啊,别不熟装熟的,攻心之计对我无用……当然,屈打成招就更别想了!”
我瞧那人的唇又掀了下:“看来楚小姐,是真的不记得在下了。”
“别越装越像的。”我厉声质问,“那你说,咱们在哪儿见过?”
青年深如黑潭的眼底波纹一荡,似是嘲讽:“不巧,咱们洞房见过。”
洞房?什么洞房?
我脑子“啪”的一声,嗡嗡作响,三年前的那桩事,顿时涌上眼前。
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,那时我刚满了离家闯荡的年纪,不仅心高,还很气傲,仗着自己是盗帅之后,在江湖很是胡乱搅和了一阵,一次我盗了武当玄玉老道那把蓄了五十年用香油宝贝的长胡子,惹得武当倾门追杀,我揣着胡子左藏右躲,眼看追兵降至,也是我命不该绝,碰到一对同样走投无路的逃婚鸳鸯。
我与新娘情郎一合计,互换了衣服,我套上新娘身上奢华的行头,披嫁衣鱼目混珠地顶替她上了花轿,而后拜堂,被送入洞房。本来就是金蝉脱壳之计,在新郎推门进来时我正夺窗逃逸,但在电光石火一瞬,我的确看到了对方那张微醺的脸。
那个人,原来便是名满天下的六扇门门主——叶恒。
得罪六扇门是什么下场?一个月前被六扇门围攻得几乎命悬一线的师兄曾经告诫我,见到六扇门的人,有多远跑多远。
门中诸多手段,以我贪生怕死的脾性,估计没一样能扛下。
我顿时蔫了,叶恒虽坐在轮椅上静静等我作答,他样貌年轻,身上却无丝毫气盛之意,并不锋利,甚至毫无棱角,仿佛历经千万次沙场淬炼才磨出的一块玉,透出一股苍茫辽远的气息,一旦被这种气息锁定住,一股莫名的恐惧和心虚不禁油然而生。
我声音微颤:“叶门主,那、那人都逃了,我也没有办法,这事是我无心之过,您大人有大量,我给您赔罪……”
“逃了?”叶恒微笑,意外地十分和善,“怎么会呢,这人,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吗?”
“啊……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“咱们可是拜了堂成了亲的,若还要反悔……楚小姐,可知下场如何?”
六扇门的人说他们这腿,是在新娘逃婚后的一次练功中因走火入魔而废掉的。
冤有头债有主,六扇门上至军师下至厨娘,一致认为这事我得负全责。
叶恒领我离开监牢时,一条精细如丝的链子由他的左腕垂下,一路顺连至我的右腕,扣在六扇门为犯人特质的手环上。
我扯了扯那条链子,找碴儿道:“我要大号小号,还要换裤子,不过门主你要是不怕臭,这话就当我白说。”
看不出叶恒生得斯文漂亮,脸皮却十分厚,他回:“去呀,子不嫌母丑,夫不嫌妻臭,夫人大可放开点。”
“……”
叶恒提的条件,看起来很简单。
休妻可以,但我必须还回他叶家传家宝,而那枚传给叶家媳妇的稀世宝石当时是镶嵌在新娘发簪上的,在我与新娘忙着偷龙转凤的时候,我压根不记得那玩意儿去了哪儿。
我耐着性子解释,叶恒自然是不信的,他听后,淡淡回了句:“你们楚门,果然早失盗帅之风,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干得太多,你以为我信?”
盗门夜留香,威名震八方,我们楚门子弟,怎能容忍如此诋毁,我涨红脸,怒气即刻涌上:“这些铜臭宝石我们楚门压根就看不上,也只有门主你才会当成宝贝藏着吧!”
“哗啦”一声,叶恒抬起手,牵连起铁链相碰:“却邪。”
我愣住,叶恒招来下属,一手闲闲握着茶杯,道:“马上昭告天下,就说楚家人在我们这儿,大伙有什么冤仇,欢迎来报。”
我立即见风转舵,忍气吞声地做敬佩万分的模样:“门主果然火眼金睛,我们楚门这些年的确出了很多败类,但请您相信,这群禽兽败类里绝对没有我!”
为了表示诚意,我甚至带叶恒回了趟本家。
小金库埋在灶台下面的一个土洞里,我撅着屁股一番好找,头上蹭了一层灰,叶恒扣在我们手腕间的东西名曰缚魂,再锋利的刀剑也切不开,而唯一的钥匙……我偷瞄叶恒的袖口,被他敏锐抓住,他的视线比网更密,仿佛没有他察觉不到的事。
我很泄气,说实话,我试过盗缚魂的钥匙。
自从叶恒将我与他锁在一起后,我赶鸭子上架地接下了一切原本属于侍女的活,对方估计是存了报复我的心思,什么杂活都得我干,片刻不得消停,前些日子,我借着给叶恒磨墨的机会,手肘假意一碰,将书册落下,在我低头去捡的一瞬间,我素手瞬翻,不着痕迹地摸透叶恒的衣袍。
坐在轮椅上的青年淡漠着眉眼,执笔批公文,仿佛毫无知觉,但就在我捡起册子,施施然起身时,叶恒看了我一下,微笑说:“夫人,是在找这个吗?”
那把解开锁链的钥匙,正虚虚地被叶恒钩在手指上。
我目瞪口呆,脑子一片空白,然后就见书房中一道弧线闪出,那救命的钥匙便稳稳落进火盆里,很快就被炭火淹没。
“哎呀,失手了。”叶恒假惺惺地拍拍手,故作堪忧,“为夫手脚不灵,夫人不会怪我的吧,不过如此也好,夫妻本是同林鸟,这回夫人总不会弃叶某而去了吧?”
诸如此类的事,数不胜数,在叶恒手上我就像孙猴子,怎么也翻不出对方的五指山,偷鸡不成蚀把米是我最好的写照。
我万般不舍地掏出了自己的小金库,递了过去。
“这是何物。”
我极为心痛,又不敢发火,看叶恒打金库,闷声闷气道:“皇帝老儿的壮阳丹……”
他“哦”了一下,又从小金库里拿起一条帕子:“这个呢?”
“秀玉谷谷主用的汗巾……”
“剑圣准备出恭用的草纸……”
“夫人的爱好兴趣,果然宽广。”叶恒迅速将小金库扔回到我怀里,他面色如常,但不出所望,我对金银兴趣不大,多爱收藏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,而金库中,确实没有他所说的叶家珍宝。
看着他这副不动神色的样子,突然觉得他有些可怜。
名冠天下,手握重权又如何,腿脚残疾,难怪新娘不愿意嫁他,宁愿翻墙私奔。
离近了些,我在他身边蹲下,顿时比他坐着还矮了不少,我劝慰他:“其实没有传世宝又怎么样啊,我赔给你更贵更好的,而且,真正喜欢你的人,谁会在乎那种东西啊。”
叶恒扬起下巴,貌似随意地侧过头看我一眼,却让我有种错觉,仿佛随着他视线扫过,我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被锋利的刀尖细细地描了一遍。
“我在乎。”他说,“那样东西,我必须找到。”
“哈……”
这是我第一次被他俯视,叶恒拿出一块绢帕,在我布满尘土的脑门上轻轻擦拭了几下,他生得斯文漂亮,双瞳明润,收起一身气势时,令人心生向往。
他指尖滑过我脸颊,我不敢动,心跳得扑通直响。
我突然觉得,那个逃婚的新娘子,也许真的是吃亏了,正这样想着的时候,却听叶恒微微低头,在耳边轻轻抛下一句令人牙痒痒的话。
“不过若是楚姑娘想多带点陪嫁,叶某还是欢迎之至的。”
临近深冬的时候,皇宫里出了件大事。
却邪在向叶恒禀告此事的时候,我还在充当丫鬟给叶恒捶腿,我捶得三心二意,一门心思都顾着偷听去了,说偷听也不恰当,叶恒想必是故意让我知道的,他瞟了我一眼:“传国玉玺丢失?能从层层守卫的皇宫里盗出玉玺,只怕有这等能耐的人,江湖中可不多吧。”
却邪也看我一眼,意有所指:“只怕又是楚家的人干的好事。”
我不怒反笑:“盗亦有道,我楚家若要盗玉玺,必会先送盗帖,定下时间,再来取之,这种偷偷摸摸的事,可不是我家干的!”
叶恒笑了:“夫人娘家有傲骨,在下佩服之极啊。”
我知他在讥我,一口气卡在喉咙里,不上不下,酿出一股子酸气,憋在心头,烧成一炉旺火,他越是看轻我,我越是想查个水落石出,证明我楚门的清白。
我随叶恒入宫,负着气,仔仔细细地察看房顶上的痕迹,研究了半天,斩钉截铁道:“这不是我楚门的轻功。”
叶恒挑眉:“如何得知?”
“楚门的轻功重在轻巧,步子落在雪上的话,脚尖点出的印子会像一朵梅花,名为踏雪寻梅,而这个,徒有其形不得神韵,纯为仿造,意在嫁祸。”
我挑衅地看着他,叶恒自然无视我的嘚瑟,随手扔了一个做工精致的小暖炉在我手上,我连忙接住,那掐金丝暖炉做工精细,里头烧着炭火,捂在手心暖洋洋。
“咦,做什么,我又不冷!”我心里怪开心的,但面子上爱逞强,万分别扭,一副十分不情愿的样子。
叶恒今日外披一件黑色裘服,领口镶一圈狐领,越发显得肤白如玉,俊美逼人,他看我半天支支吾吾,便哼了一声,自己推着轮椅往出宫的方向驶去,淡淡地留下一句:“留着多捂捂肚子,别过几天又疼得颠三倒四血流成河的,搞得像我家暴一样。”
事实证明,叶恒有一张乌鸦嘴。
失窃案子用那些手法逃不出我法眼,这几日我随他去宫里办案,大概是真受了凉,月事来的时候简直疼得肝肠寸断,几度晕厥,晕晕沉沉间,有人端药进来,强捏我鼻子一口一口咽下,叶恒将碗收在一边,面无表情地拿出一套银针。
我缩在床上,瓮声瓮气地问:“你,你要干吗,乘机报复吗?”
叶恒听了,反而将银针举得更高:“给你止痛,你体太寒,不趁着年轻调理,老了有得你受。”
体寒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,我生时未足月,我娘那副娇娇弱弱的身子没撑住,生下我后就去了,从此我是盗帅嫡系子孙里唯一的传人。
楚门一向以盗帅嫡亲自诩,重门第,讲规矩,我从小就被长老们寄予厚望,他们试图培养出惊艳绝伦名震江湖的盗帅之后,但事实残酷,我天赋平平,加上体弱爱病,大伙便渐渐对我失了期待。
但凡是人都会有几分血性,我也不例外,一旦六扇门逮到我的消息传出去,楚门在江湖中,必成笑柄。
所以……我再也不能给楚门抹黑了啊!
叶恒擅医理,几针扎下,腹痛似乎真有改善,我趁机滚出一串眼泪,凄凄惨惨地缠着他,扯他衣袖,死活不撒手:“叶门主……你给个准啊。”
“就是不给。”叶恒斯斯文文地收针,他手掌盖在我眼前,声音是少有的温柔,像初春的溪水,自有一番温热,“苦肉计对我没用,不过,美人计或许能管用,夫人下次大可试试。”
“……”
叶恒大约真是个面冷心热的人,嘴上损我不留情面,但夜晚却将公文搬到我这边,办公守夜两不误。
翌日醒来,叶恒的心腹却邪奉命过来送药,这汉子就是当初抓到我的那位,对我相当有成见,觉得我是一坨顽固的老鼠屎,黏着他家英明神武的门主,我听他抱怨,他说自从我来后,门主越发少去门中找兄弟们喝酒了,果然美色误事啊!
咦,何时我也有了美色,不过转念一想,在如同和尚庙一样的六扇门里,我如今可不就是独一枝的美色吗?
叶恒在“和尚庙”里办公,那必然会身正影正,估计连寻花问柳的机会都没有。
不知为何,一想到这个可能性我就怪开心的,却邪瞪我,打击道:“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,我家门主对谁都是很好的!”
我趁机打听:“兄弟啊,叶门主的腿你们认真找医师看了吗?我认识好几个神医,可以……”
却邪愤愤打断我:“没用的,御医当年都来过好几回,过门的媳妇跟人私奔门主颜面尽失,加上那会儿又是门主嫁衣神功第八层突破的关键时刻,走火入魔,双腿经脉尽断,哼,说到底都是你的错!”
却邪的愤怒言犹在耳,我的心口就跟挂了一块铅块一样,拼命下沉。最早的时候我不是没有愧疚,但更多的是觉得,自己不过是推波助澜,都是阴错阳差,那王小姐早就决定了私奔,没有我,她难道就不走了吗?
但每每一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叶恒,那股愧疚就如同墨点,洇开在纸上,停不下,止不了。
临近傍晚,我提了食盒去叶恒办公的地方,那是六扇门西侧的一处偏殿,大约是地龙烧着的缘故,叶恒腿上没搭毯子,我趁着摆盘子的机会,多看了几眼他的腿。
叶恒挺诧异的,桌上摆着四菜一汤,外配三款点心,他狐疑地打量我:“咦,你做的啊?”
我挺胸抬头:“当然是我,就你们六扇门只会做馒头夹辣椒的厨娘,做得出吗?”
“哎呀。”叶恒挑眉看我,眼角笑出细微的纹路,“别是金玉其外就好了。”
他就嘴上硬,最后还不是把一桶饭都灭得一干二净,这些菜色是当年盗帅身边的宋甜儿传下来的,我在习武上天赋平平,厨艺方面却大有斩获,我抿着笑,看着叶恒夹菜喝汤,埋头苦吃的认真模样,忽然觉得所有烦恼一扫而光,只留下充盈的快乐。
为什么看到他,就会觉得快乐呢?
若他能更轻松,更快乐,更健康就好了,若我能为他分担一点,不用太多,只要能让他眉头再舒展些许,就好了。
于是在叶恒用完最后一块点心后,我下定决心,对他说:“玉玺……你想要玉玺的下落的话,我帮你吧。”
六扇门早就怀疑,失窃的玉玺在俊王府中。
俊王手握兵权,有夺权之心,与皇帝剑拔弩张并非一日之事,只是面子上没捅破,六扇门又是公门,不好去探,我自动请缨,自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叶恒没答话,我们四目相接,他瞳仁漆黑,润泽如雾,仿佛水光潋滟,激得我心口一热。
我故作不在意地笑,我说:“不过呢,我也是有要求的,若成功,那叶门主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呀。”
“但说无妨。”
他一定是以为,我会提出离开的事,但这回他可估错了,我笑嘻嘻地看着他:“若我回来,劳烦门主随我一起去探望下诸葛神医吧。”
盗亦有道,这句话并非妄言。
朝廷的事我从不掺和,但为了叶恒,我愿意破例,不只是愧疚。这夜无星无月,宽广的天幕似一张巨网,黑得密不透风,俊王府不愧是当今仅次于皇宫的地方,里面机关林立,院与院之间布有鸳鸯连环阵,若对五行八卦毫不知晓,只怕会彻底迷失最后丧失神志。
我用了大半个时辰潜入,果然寻得玉玺,还在密室中找到多张俊王与朝廷宦官、大臣们密通的私信,我急急将证据收进怀中,进府容易出府难,突围时我背后不小心中了一枪机关暗箭,没伤到内腹,只是血流不止,在逃到一处僻静安全的地方后,终于是头晕乏力地晕了过去。
再次醒来时,一位梳着妇人头发的年轻女子正端着药,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。我全身戒备,那妇人见我醒来,露出欢喜的神态:“姑娘不可乱动,你中了毒,要好好休养着。”
我突然觉得,眼前的妇人竟有几分眼熟,那妇人笑得温婉,她说:“姑娘可是不记得我了?”
我目瞪口呆,眼前这人,可不就是三年前,与我互换喜服的那位吗?
原来王家小姐逃婚后就与情郎隐居在此,日子清贫,我对叶恒生了情意,便不动声色地打听:“王家小姐可曾后悔当时决定?我听说,当年叶门主对王小姐可是极好的……”
妇人苦笑:“姑娘你不知道,那桩婚事,都是家父家母为一时荣华迷昏了眼罢了,我与叶家公子,是半点情分都没有的——”
她这话听得我怪不舒服的,我不解:“叶恒贵为六扇门门主,年轻英俊,诗词琴艺天文地理无一不通,又哪里委屈你了?”
妇人神色淡淡:“我王家不过普通人家,那姑娘难道没有想过,如此年少有为的叶家公子,为何会与我定亲吗?”
“……”
她见我一脸茫然,露出一抹古怪至极的笑:“那是因为,叶家的男子,皆活不过四十啊!”
江湖野史称,神侯叶家历代修炼嫁衣神功,神功霸道,易遭反噬,功力越深,反噬越强,习此功者,命皆不过四十。
我愣愣地坐在床上,脑子乱成一片,我告诉自己不能听信野史与她的一面之词,世界上机缘巧合的事多了去了,哪有那么多要人命的邪功!
在我昏睡了三天中一个消息都没送回去,只怕叶恒是等急了,我不顾夫人好意,一心要走,走之前我将手头值钱的东西全都留给了夫人,我说:“这些财物够姐姐好好过下去,既然姐姐已经嫁作他人妇,叶家的传家宝……能交给我吗?”
也许是王家小姐的话,让我多留了一个心眼。
我一个人静静回了六扇门,没惊动任何人,烛光由叶恒办公的那间屋里透出,叶恒面前跪着数个捕头,他握着茶杯,喜怒难辨:“人还没找到?”
却邪回:“尚无,但俊王府里并没有捉到她,属下觉得,她是借此机会逃走……”
我趴在房顶上,里面的话听得一清二楚,透过缝隙,只见叶恒微微笑了一下,说:“不会的,她对我有情意,人又不太聪明,不会乱跑。”
“但是……”
“记住,这件事,不能经我们的手。”
是啊,我的确不聪明,我直到刚刚,才知道什么叶家只传给媳妇的传家宝,不过是个谎言。
离开时,王家小姐告诉我,她从未听过什么传家宝,当时叶家聘礼中,只有金银数箱。
我鲁莽地推开房门,房中数人露出诧异的神色,“啪”的一声,我将玉玺、几封密信全都扔在地上,叶恒的视线落在染血的信封上,眼神微动:“你受伤了?”
我哑着嗓子,声音近乎错乱,仿佛所有情绪都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:“你回我,叶恒……你当初留我在身边,是为了什么?”
为什么要编一个这样的理由困住我?为什么要同意我去俊王府里盗玉玺?我隐隐察觉到在这个局中,我,包括我身后的楚家,都是他手头的一颗棋子。
而在我之前,楚门数位师兄都恰巧被六扇门围剿过,但都被他们逃脱。
只有我,我天赋平平,成了瓮中之鳖。
“抱歉,其实之前我有与你们楚家族长谈过合作,都被拒绝,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。”叶恒转动轮椅,看向窗外夜色,“俊王府固若金汤不是秘密,为俊王府布阵设机关的人是夜帝一系的传人,而当年盗帅师承夜帝一脉,世间能破夜帝阵法的,唯有楚家一门。”
难怪,难怪叶恒要借着找传家宝的名义去我楚门,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我想起这几个月的点点滴滴,包括我们一起生活,一起吃饭,互损胡闹的场景,明明很真实,每一幕都很清晰,但串起来一想,却又模糊得远在天边。
“哦,我懂了。”我笑得比哭还难看,“你都是在骗我吗?那你告诉我,你有什么是真的?”
叶恒的神色有一瞬间的痛苦,但只是一瞬,他片刻就收整好情绪,静静地问我:“你觉得呢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惶惶回道,“有人说……说你们叶家的男人,只能活到四十,是真的吗?”
“是真的。”叶恒抬起手,卷起自己的衣袖,白皙精瘦的手臂上,数条经络清晰可见,仿佛烙印,“嫁衣神功,经脉逆行,我早已时日不多。”
我用颤抖的手指碰他的手臂,突然就不怨他了,我泪如雨下:“那,那我陪你到四十,好不好?叶恒你别怕,我陪你到四十……我,我去给你盗少林的《洗髓经》,我不怕十八铜人阵,我给你治……”
他收回手臂,摸了摸我低垂颤抖的脑袋,动作轻柔,声音无情,这大概才是六扇门主人真正的模样,冷酷绝情,不容半点怜悯。
“谢谢,不过。”他说,“我并不需要。”
叶恒果然说到做到,一副用完的抹布要快点扔的架势,命却邪将我押送回了楚门。
楚家长老知晓了这事的来龙去脉,没揍我,就是命我在房闭门思过三个月,夜里我辗转反侧,脑子里里外外都是叶恒的样子,我取出叶恒那日给我的小巧暖炉,睹物思人地捧着,因为看得仔细,这才从炉子侧面的一处隐秘雕纹里,看到一行极细小的字。
制于徳宣二十五年冬,特赠欢欢。
我茫然,如果他真不喜欢我,为什么要亲手做这个给我,长老曾说,江湖险恶,有时你的所见所闻并非是真,那我能不能欺骗自己,叶恒的冷漠也是如此呢?
禁足解开后,我没去六扇门找叶恒,而是去了趟少林寺。
我给思佛方丈带了时下最新最热最火的畅销书,思佛方丈礼尚往来,请我吃了他新炖好的肉酱猪蹄,我拜托他,我说《洗髓经》不是专治走火入魔的吗?大师你就借我看看嘛,救人一命,功德无量啊!
大师唾弃道:“别欺负大师我没谈过感情,你是想救哪家儿郎?”
我说:“哎呀……就是六扇门的当家啦,不过是我是单相思而已,但只要青山在,我就有能烧柴的那天嘛,哈哈。”
大师诧异:“六扇门?六扇门上个月不是与俊王府勾结,叶家小子不是早被皇帝清理门户了吗?”
这时我才知道,六扇门因为一个月前的那场围剿与大火,彻底变成了一堆废墟。
据说禁军围剿那日的大火,足足烧了一个晚上,最后在门主办公的屋子里,找到了叶恒的尸体——双腿断裂,被烧得样貌模糊。
所有人都劝我,说叶恒死了,六扇门为朝廷鹰犬,飞鸟尽良弓藏,哪任门主不是如此下场?
已是春季,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瞎逛,来到了我与叶恒初遇的地方。
王家人早已搬走,偌大的宅子空荡荡的,没有一丝人气,我寻着记忆来到当年那个婚房,虽春意暖暖,我依然抱着那个小巧的镂空金丝暖炉,炭火噼啪裂开,手心一烫,暖炉咕噜咕噜地顺着屋外的斜坡往下滚,我赶紧小跑着去捡,这时,入目的是一双熟悉的手,轻巧地捡起暖炉,指尖钩在丝带上,那人站在屋外的一株杨柳树旁,黑袍绲金边的袍子,笑意盈盈,乌发如旧。
这一刻我很恍惚,我不知道面前的人是真实,抑或是自己长久的思念妄想出的幻影。
“叶,叶恒……”
那是叶恒,一样的眉眼,一样的微笑,他迈着稳健的步子,朝我走来,他个子原来是这般高大,收拢双臂时,压得彼此肋骨隐隐作痛,但是这没人在乎,彼此心跳清晰,仿佛是用着同一颗心。
“傻瓜,别哭了,快笑啊,我最喜欢看你笑了。”
我哭得止不住,我说:“我以为你死了,大家都说你死了!”
叶恒在我耳边轻声道:“没错,六扇门门主叶恒死了,但我活过来了,从今日开始,我便是你的了。”
叶恒告诉我,为了这一天,他叶家已经准备了整整百年。
自太祖立国后,叶家便掌六扇门,神侯叶府为朝廷鹰犬替帝王做无数肮脏的,秘密的,见不得人的事。
但知道得太多,便如深陷泥泞,叶家先人便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,他们命人私下传出,习嫁衣神功者四十暴毙的消息,而每任门主都严格地遵守着秘密,到了差不多的时间,他们便会安排好一切,吞下假死药,自废武功,做出经脉尽断的假象。
“皇帝多疑,唯有这样,才能瞒过他的耳目,到我这辈……我却不想这样下去了。”叶恒语气柔和,眉目间自有一股坚韧锐气:“六扇门的兄弟我早已安排好,这个地方太脏,我的兄弟们,应该有更好的生活。”
所以他一直在等,等一个彻底解脱的机会。
三年前,叶恒早就知道王小姐逃婚,他命人暗中帮助,助他们安全脱逃,远离是非,而他又可以以此为幌,打着“怒极攻心,走火入魔”的名头伪装腿残,皇帝早有杀他灭口之心,在他收集完俊王谋反之事后,就是皇帝清剿他的时候了。
百年忍耐,三年伪装,终于在大火呼啸而起的那一刻,彻底落下帷幕。
而这场棋局里,他说唯一的没想到的,便是我的出现。
听他这样一说,我心里暗暗满足,面上却恼怒起来,他现在人比我高,身子比我壮,我拳拳揍去,他也招招受住,我说:“你这个骗子!居然还骗我给你天天洗脚,你说,为什么我抠你脚底板你一点反应也没有!”
叶恒摊手:“我怕痒的地方不是那儿,你要是想知道,以后夫人可以多摸摸啊。”
我扑哧一声乐了,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,在宋甜儿传下的菜谱里看到了一段百年前她无意间写下的话。
她说,一个人在世上,若遇到另外一个能让你觉得快乐的人,那请你一定要留住。
所幸,我已经找到了他。
(文/小禾苗)